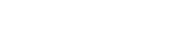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近两年,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一直是国内高教界最为关注的话题。2 0 1 6 年年底,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高度概括了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在实施“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落实好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推进立德树人实践,培养出一流人才,这是个重大的命题。
“双一流,,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曾经多次讨论“双一流”建设,显然,“双一流”并不是“9 8 5 ”和“2 1 1”的简单重复,而是国家进步对于高教发展的一种新要求。从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也可以看到,自2 0 世纪7 0 年代起,我国教育投入的比例在逐步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我国髙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科技实力不断提升。近2 0 年来,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从1 9 7 8 年的2 . 7% 提升到2 0 1 6 年的4 2 . 7 % 。这个数字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密不可分的。
无论对于学科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还是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髙等教育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受髙等教育发展等因素影响,我国科技实力持续提升,科技期刊论文数不断攀升,现在仅次于美国,已超越其他“G7 ”国家,位居全球第二。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世界第一,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居全球第二位,在大众化、综合化、高水平化和国际化等维度上,中国高等教育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然成为高等教育大国。特别是在国际化方面,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 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829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5年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其中自费生393751人,占来华生总数的88.93%。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就。
在这种形势下,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启动了中国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是在过去“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成绩上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目标是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从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在国家“双一流”整体方案规划下,北京大学围绕“世界著名的学术殿堂”这一建设目标,提出了“30+6+2”学科建设项目布局:面向2020年,建设30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面向2030年,部署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医学等六个综合交叉学科群,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面向2048年,布局和建设两个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即“临床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带动学科结构优化与调整,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使命
目标确定,我们冲锋的号角也已吹响,如何实现?在我看来,大学之本在于人,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尔认为,“对一所大学来说,再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使命。假如大学都不能承载这一使命,我看不出社会上还有哪家机构堪当此任”。
然而,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大学所肩负的多重任务似乎挤压了人才教育的空间。其实在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成立之初,其教育理念就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也是公认的近代大学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而如今,现代大学的发展却逐渐背离了初衷,很多学校呈现出重科研轻教学、重专业轻通识的状态。我认为,未来应重新树立教书育人在大学的基础地位,强化体系建设,强调通识教育的应用,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跨学科人才。
具体到医学教育方面,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有一个全局性的思考。可以看到,在北大“双一流”建设的目标里,“临床医学+X”是两个前沿交叉学科领域之一,是北大“双一流”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此前提下,我们提出了北大医学这个核心概念,也就是在北京大学的框架内,无论是过去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还是北大本部的生物医学相关学科,都统筹在北大医学这个概念下,作为一个综合学科围绕生命进行研究。北京大学力图以此类改革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其中,在临床医学方面,注重协调学科平衡,加强全科、老年等急需学科发展;同时建设肿瘤、心血管病中心,注重前沿学科发展,为国家全球健康战略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在交叉学科方面,成立健康大数据研究院、医学交叉研究院、多组学研究中心等,以此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
医学教育要注重方法的传授
回望医学发展的历史,2 0 世纪50 年代以前,我们可以称之为经验医学时代,其核心是个人经验的传递,即“传帮带”,相当于师父带徒弟。而循证医学(E v i d e n c e -B a s e dMe d ic i ne)的出现,标志着医学界以临床证据的形式融合群体的经验,科学化的临床研究成为医学进步的重要推手,疾病的科学分类也变成了可能。而当前我们已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出现了信息化与智能化趋势,把人工智能融入医学,可能会带来医学上的革命性突破。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精准医学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在规范化治疗的前提下,对患者以个体为单位进行个性化医疗。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疾病的分类也有了新的认识。以肺癌为例,现在我们认为肺癌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类型,而其中部分类型的生物学基础或者治疗方式又跟结肠癌、胃癌或者肝癌有关联。这就打破了过去相对呆板的疾病或者学科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疾病,从而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帮助。
比如,传统上外科治疗就是“三板斧”,简单来说就是开刀,手段也比较局限。到了循证医学阶段,很多外科技术出现,但是外科依旧是一个个孤立化的模块,治疗依然基于术者个人的特质。包括现在的内科、外科、胸科等分类,都是我们对疾病浅显认识下的孤立分科。例如,一个人视网膜出了问题,在不同医院的眼科反复就诊,但最后视网膜还是脱落了,他不知道引起视网膜病变的原因有很多,脱落也可能是糖尿病造成的,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在现实中,临床上有大量的病人徘徊在人为造成的科室壁垒之间。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精准医学的出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我们不愿意把华生医生(Dr.Watson,程序自动保存系统)和阿尔法狗(AlphaGo,人工智能程序)解读为机器替代了人,而是将其看作人类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现代技术不断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随着医疗信息技术的进步,既往孤立化的医学模块将会被整合,患者就医治疗不再受限于一个人的知识和见解,而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网络化模块的综合,给出最适合患者个体的治疗模式,对数据的利用和解读将成为医生的核心能力。
这种医疗模式的改变向医学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传统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可能难以应付现在的要求。我们要不断反思,年轻医生通过接受8—10年的专业培训到底能不能应付未来三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因此,医学教育要格外注重方法的传授。尤其在当下,循证医学是医疗行为的基础,目前我们的医学教育已经非常重视告诉学生证据是什么,但在对证据的理解包括如何获取和利用证据等能力的培养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医疗本身正在发生剧变,但现在医学教育对于跨学科研究及学习能力的培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学生为本进行医学教育
我们要建立新的课程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师学院( RC P S C) 于上世纪9 0 年代提出医生综合能力培养模型,倡导以医学专家为核心,学习包括交流、合作在内的领导能力,培训其扮演健康倡导者、职业人等在内的不同角色。在中国,北大医院率先与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师学院合作,在国内开展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住院医培训,并通过协会的机构认证。
在教学工具上,新的信息技术为我们获取信息和模拟式教学提供了更多可能,如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可明显缩短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时间,而对照组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此外,评价手段或考核方式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直接影响,起到引导的作用。在新的课程模式下,我们需要结合工作场所,进行整合式的评价。目前很多医院在临床上已经开展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和迷你临床演练评估(Mini-CEX,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应用效果很好。
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必须有相应的一流教师,这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医疗体系存在过分强调科研的现象,教师忙于发论文、评职称,这与我们现在的医学发展潮流并不符合。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注重对教学活动的奖励和支持,医疗教育不是医生的副业,加强培训体系和师资的建设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重点。另外,我们要深化人文教育,立德树人。这不仅意味着要体谅患者,同时还要注重强化和引导患者在医疗行为中的主动意识,建立新型的医患共同决策体系。
虽然我国西医院校的发源和体系构建都来源于西方,但最终的临床实践一定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这意味着用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西医会存在认知上的偏差,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学习西方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西医;同时,我们需要系统地了解西医在中国的沿革,这有助于中国未来的医疗领军人才更好地理解西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本土患者。
(统战部摘自【群言】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