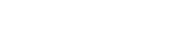61岁的马弘曾是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的队员,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她还参与了洛阳大火、大连5·7空难、SARS爆发以及天津爆炸等几乎所有国内大型灾难的心理危机干预。
每见证和参与一次患者灾后从毁灭到重生的过程,马弘心中的希望感就更确定一层,「人类是可以在灾难中走出来回归到正常生活的。」生活中遇到难过的坎儿时,她也安抚自己,「等一等,事情可以重新开始的。」
太乱了。心理服务的帐篷像是从裂开的地缝里长出来的,出现在绵阳、成都等地震灾区。穿得像越野战士一样的心理咨询师们坐在那儿,旁边堆着与往常一样的宣传资料——如果你有心理问题,请打我们电话预约。
「那会儿老百姓着急找人找吃找喝,手机没电,甚至手机都找不着了,谁跟你预约什么咨询,不是瞎扯嘛。」回忆起10年前汶川地震后各种心理咨询团队纷纷涌入灾区的情景,马弘双臂折叠着压在咖啡桌上,眼皮往上一翻。
「有那种流动的来了就发表格,把人家睡着觉的灾民给摇醒了,然后填表。」马弘说很多灾民和志愿者管这些人叫「杀手队」。还曾有两名受灾儿童因慰问团开的「空头支票」差点自杀。「说将来带你们去香港发展呀,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呀。」但说完就走了,未被兑现的承诺再次剥夺了他们的希望感,这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大忌。
当时身为国家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队长的马弘,看不上这种不专业的心理服务。这位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六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现年61岁。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她成为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的队员,此后又参与了洛阳大火、大连5·7空难、SARS爆发以及天津爆炸等几乎所有国内大型灾难的心理危机干预。
到达地震灾区的第二天,马弘就开始召集志愿者,捐款买书买花买凳子,还有体育老师带着小足球,被吸引过来的小朋友在帐篷前围起了圈。台阶下的家长也因孩子变得活跃而显出开心。儿科医生趁着跟孩子玩儿的机会,一个个聊天做了筛查评估。
「就跟他们玩,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有书读,有画画,这个就是干预。」马弘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此前,当有小朋友讪讪地说出没有短裤后,马弘意识到这种生活用品缺乏给他们带来的窘迫。她马上向外界发出需求信息,第二天,整整一卡车的T恤、内衣、牙具等,就直接送到了当地的临时指挥部。
「没出3天,所有的心理咨询队伍都改得跟我们差不多了,到处小朋友都在看书,在玩儿,在踢球,生活开始恢复了,就觉得挺好了。」马弘感慨,「中国人学习能力真的特别好。」
尽管存在太多不正规、不专业的现象,但在马弘看来,汶川地震后大批心理咨询团队能够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仍然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毕竟,在地震之初,是否要将灾后心理干预的国家队派往现场,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72小时再不去,小心这些人将来得创伤应激障碍。」马弘当时对卫计委领导说,而彼时他们正忙着派出常规医疗队。
「心理救援也有黄金72小时吗?」领导问。
「当然有了,第一时间救援总是最好的。」其实,马弘也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但好在她很快就被同意组队去灾区了。
参与完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的心理危机干预后,马弘成了队伍的组织管理者,按她的说法,是因为自己人脉好,每次无论卫计委、儿基会还是联合国要求组队出任务时,都会找她。接到任务,马弘就开始自己组织队伍,找的都是自己认识的精神卫生领域经验丰富的医师。马弘说,「那时候组队真的不怎么正规。」
在马弘看来,相比汶川地震中的集体行动,2003年的SARS是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在大众意识中的一次全面唤醒。
她还记得,当时宣称SARS会导致焦虑的报道到处都是。「本来只是说人遇到灾难,会产生焦虑、忧郁」,但文章一多,就好像SARS必定导致焦虑。「那会儿大家还不太掌握这个。」但令马弘欣慰的是,这让媒体的视线迅速对准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
疫情的特殊时期,除了常人对患病的恐惧与焦虑,被一套穿戴严密的防护服割裂的医患关系,也致使双方各自忧虑——患者无助,医者无奈,因为他们无法交流,进去打完针就走,这是规矩。
马弘代表医护群体给所有患者写了一封信,「我们和您一样,都是第一次遇上这种疾病??平时,我们会用微笑缓解您的不安,今天,厚厚的口罩挡住了我们微笑的面容??」
她特意选了粉色的纸张和信封,但当时北京市负责精神卫生的领导却不肯用。急脾气的马弘跟领导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气得一屁股坐折了椅子,把椎间盘给墩碎了,上了手术台。但好在后来通过中国护理协会,这封信还是向所有医院发出去了。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马弘仍然认为当时发出的那封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信息才能打消疑虑,所以这封信的传递像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撒下的希望的种子。患者在无望中获取希望,知道自己是被关注的;医护人员传达出自己的关切,基于职业规范下的负担被放下,轻松上阵。
这种极强的换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精神科磨练了若干年之后,马弘才学会的。
1980年代入行之初,马弘就见识了一系列因国民经济不发达而造就的抑郁症患者,「老太太家里丢了一只鸡,就神经症发作了,抽得不行,一大家子赶着马车把她弄来。」马弘脊背宽厚,双手戳在讲台上,在北大医学部的研究生课堂上讲起当时的不以为意。「一个副所长跟我说,你以为一只鸡就是一只鸡,那丢的是他们家的银行,塌天的灾难。」
「这也算事儿」的嘀咕从马弘心里逐渐隐去,到后来她甚至会站到对方立场,帮其说话。然而,共情是没问题了,将患者与自我在情感上隔离开,却成了马弘的七寸之地。1994年去克拉玛依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时,马弘就掉入了「替代性创伤」的陷阱。
那时马弘已是从业11年的高年资主治医师。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大火,288名学生和37名老师、家长及工作人员死亡,132人受伤。
休克、晕厥和要自杀的遇难者家属被一个接一个地送进油田总医院的急诊室,都是心因性反应(即急性应激反应)。坚持了两周,药没了,医生也扛不住了,院内工会主席经石油部向卫生部请求派出心理专家。
指令传达到3000公里外的北京,六院30多名医生报了名。马弘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当初的自己也跟2008年挤着去地震灾区的心理咨询师心态一样,想要经历,想要大显身手。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吕秋云最终在写满名字的大白纸中挑选了「热情高、愿意做事」的马弘,到当地进行「心理帮助」。
后来,这次援助被看做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开端。而当时,无论是曾在美国学过心理与家庭治疗的吕秋云,还是科里的精兵强将马弘,都觉得心里没底。
坐在一辆污渍斑驳的三菱帕杰罗上从覆盖着白雪的旷野穿过,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这六七个小时的车程,马弘觉得冷、期待和不确定。下车后,司机告诉他们,车上的污渍是火灾遇难者的身体渗出液,他们的通俗讲法是「人油」。
接待的小伙子径直将马弘和吕秋云引向医院宣传科,放火灾时的录像——孩子在里面砸碎了玻璃,却被外面的铁栏杆截住,家长在外面喊,孩子在里面叫。绝望的气息溢出画面。
画面中,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平躺在清真寺里,有的头上还扎着俏皮的小辫子,大火没有烧毁他们的演出服,黄色、绿色鲜亮得扎眼,他们大多死于窒息。家长哭嚎着从这些闭眼的小人儿里找自己的孩子。马弘越看心越紧,到第4个小时,胃疼得出去吐了。
病房里的小女孩举着烧成「小黑棍」的10根手指转来转去,满怀希望地跟马弘说:「阿姨说了,给我装假手,会跟我原来的手一样漂亮。」「我都不敢再问了,我也没法骗她,那假手没功能。」马弘没法设想她今后的人生,她觉得绝望而挫败。
尽管出发前马弘做了很多准备,但最没想到的就是自己会受多大影响。遇难者家属的麻木、懊恼与悔恨,爬到马弘身上变成了愤怒。快过去24年了,回想起这些时,马弘依旧恨得咬牙切齿。
马弘强烈的同情心让她更易与别人共情,吕秋云告诉《人物》记者,「她有时候比家属、比病人反应还大。」马弘开始睡不着觉,易怒。吕秋云就拿出自己带的录音机,两人一人一只耳机听歌,让彼此都放松下来。
从克拉玛依回来后,无论逛商场还是住酒店,马弘会下意识地找灭火器和消防通道,设想灾难下的逃离方法;她开始搜集各种灾难信息,分类归置在电脑里;她对上门拜访的客人展示克拉玛依的照片,一遍遍讲那些故事。6年后,一位澳大利亚专家将她的这些行为判定为「耗竭综合症」。
随着经验的逐渐丰富,马弘越来越能让自己在干预过后尽量短的时间里恢复常态,但直到2015年的天津爆炸事件,马弘也依然无法将自己与事件完全分离开。每次出任务回来后,她都要约吕秋云聊上一两个小时,对自己进行疏导。
她记得,一名在克拉玛依大火中下肢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光着下身躺在病床上,嘟囔着「早知这样,还不如光着屁股在山上放羊」。她很少看马弘的眼睛,但说到「北京」时女孩眼中闪过的一丝光亮被马弘抓住了。
希望来了。马弘问她有没有去过北京,小女孩答没有,想去北京看熊猫。回来后,马弘满北京找卖熊猫玩具的地方,没有买到,最后买了一只棕色的毛绒熊寄给了小女孩。
一年后,马弘收到女孩来信,感谢她当时的谈话与寄去的玩具熊,那给了她很大的支持。陪伴,并给予希望,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这两大原则是在此后被总结出的技巧与经验,但那时候的马弘,是在对此没有明确意识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两点。而那封信,是马弘收到的第一份确切反馈,让她知道,「哦,原来现场支持是有效的。」对于这些受难者来说,他们太需要物质与心理的支持,来抵消那些亲人、身份与尊严等混合在一起的巨大丧失感了。
然而,并非每一次的干预都是顺利的。地区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都造成了社会对心理危机干预认识与接纳的不同。比如2000年河南洛阳的老城区东都商厦大火,和2005年四川达洲、云南文山州、黑龙江沙兰镇等5省自然灾害,马弘和吕秋云也带队准备去做心理危机干预,但都被当地工作人员挡到了一边,「我们这遭了灾,老百姓没得精神病,没疯,疯了才找你们呢。」
而联合国儿基会为每所被自然灾害损毁的学校配发的5万美元重建基金,却被要求留下,「你把钱留下,你们在这儿玩两天就回去。别打扰我们受灾群众了,我们挺好的,就缺钱,不缺心理服务。」
「人家不欢迎,当地没有意识。」吕秋云告诉《人物》记者。马弘则憋屈得喊「冤」,「国家这块完全不重视啊。」早年间,大众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时,对身体上的硬伤病的治疗还是奢侈的需求,精神疾病就更排不上号了,社会对精神病甚至精神科医生都带有潜在歧视。
35年前,因对病人奇思妙想的好奇和父亲友人的指点,马弘选了精神科,成为那个年代不足一万人的精神科医生中的一个。那时,学医的很少有人会主动选择精神科,街坊甚至质疑马弘「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才去了那种医院」。
随着社会对精神类疾病的耻感逐步降低,当初闲得能聚在护士站嗑瓜子聊天的每天100个左右的门诊量,现在已经涨到了日均1600。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也名正言顺地进了「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如今,各地的心理干预救援队伍都已开始组建。
最近,马弘正忙着用自己编写的实训手册,给各地新成立的队伍做培训,每天在各种学术国际会议、项目的启动设计与各种培训教学中奔来跑去。
每见证和参与一次患者灾后从毁灭到重生的过程,马弘心中的希望感就更确定一层,「人类是可以在灾难中走出来回归到正常生活的。」生活中遇到难过的坎儿时,马弘也安抚自己,「等一等,事情可以重新开始的。」
(摘自人物201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