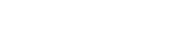你不会想到,一个全身多部位转移的肿瘤患者,跟着医生闯过一关又一关,4年多了,无癌生存。这位患者是沈琳身边的同事,也是一位医生,她甚至天天看着他正常地工作与生活。
对此,沈琳的幸福感强烈到无法形容,不停地说:“真的好,真的好,你只要看着他,就快乐!”
这位出生在江苏徐州的女医生,外表依然保有江南女子的风韵,性格却早已褪去了江南女子的柔弱,不仅带领着国内消化肿瘤内科的学术发展,还担任北大肿瘤医院副院长,跻身男性为主的医院管理界。
十年来,她发起并主导的肿瘤多学科协作组(MDT)从一个医院走向全国。如今这种多学科医生坐在一起,为一个患者讨论制定最优化的治疗方案的工作模式,已在国内肿瘤医生群体中遍地开花。
在沈琳院长的办公室里,轻松地聊着MDT,聊着1992年读研后第一个暑假,揣着3000块钱做了26天“背包族”的壮举,她哈哈大笑,简单快乐的像个孩子,说自己就是个粗线条的“粗人”。
和肿瘤医生聊天,绕不开生死。
她陷在对面的椅子里,回忆起20多年前遇到的两个与自己同龄的患者,不知不觉毫无保护性地一头扎进了共鸣共情中。当他们终因肿瘤无法控制面临死亡时,医生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让她很多年都走不出来。面对大部分“没有未来”的晚期肿瘤患者,日复一日,她淡淡地说:“我再也不和患者交朋友。”然后,不动声色地拭去眼角的眼泪。
医路走来32年,沈琳变成了“沈阿姨”,学会了在同理心中自我保护,也学会了用更扎实的医疗技能,尽力地去为患者创造生的希望——这种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幸福感,无论对患者还是医生,都弥足珍贵。
01肿瘤医生的幸福感
患者本来是没有希望,但通过医生的治疗,重新充满了希望,而且状况一天比一天好,最后甚至有机会做手术、做根治性治疗,这样的幸福感,是医生源源不断的动力。
对医生来说,记忆最深刻的是让自己懊悔、痛心、痛哭的患者,而支撑他们往前走的,则是那些让自己喜悦、骄傲的患者。
沈琳:
发小找到我时,诊断是直肠癌,检查后发现已转移到肝,12个病灶弥漫每一个肝段。我心里那个难受啊,这个人是你儿时记忆里的一部分。
他说:反正我一发现得了肿瘤,我就来找你了。这份特别的信任,会让你不顾一切要去救他,他也全力配合,让医生充分运用所有的知识、技术与新理念进行综合治疗。
这中间遇到很多问题,毕竟是晚期,又要放化疗,又要手术,很复杂,治疗了很长时间。手术后还出现各种合并症,肝漏、胸腔积液、直肠吻合口漏,复查时,又发现新的病灶……
每一个过程都让你揪心,现在回头去想时好像又不那么复杂了,但在进行中时都是很难判断很难作出选择的,摸索中经历了各种纠结和风险。
你会跟着他的悲而悲,跟着他的喜而喜。
终于,通过你所有的努力,两年多了,肿瘤消失啦,他活得很好很快乐幸福。
这样的患者,你什么时候想到,你都很幸福。
02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倒数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倒数,只是我们的倒数不可预计;而肿瘤患者,尤其是沈琳遇到的中晚期肿瘤患者,他们倒数的步伐更近更快。
对生命,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而当一个人具备把生命的“可预计”变成“不可预计”的能力时,他会对生命更加渴望。这就是肿瘤科的医生,总是希望自己的患者,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活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抓住任何可能治愈的机会,这是医生职业的素养与要求,也是人对生命追求的本能。
实现这些目标,这除了医生本身的能力,更需要家属、患者共同努力共担风险,也需要政策的支持。
沈琳:
我们曾遇到过一个大出血的50多岁的胃癌患者,黄疸,肝脏弥漫转移,胃里满满的血,大量呕血,血色素只剩五克。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患者会迅速死亡,即便止住出血,也只能活几天。
但我们分析后作出方案,如果能抓住瞬息即逝的机会,给予同时止血抗肿瘤治疗,他也许能闯过这危险的一关,也许他还能生存一段时间。
这个方案的风险很大,只有30%的可能性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不做就没任何希望,这需要医患共同协作和彼此信任。
后来,患者和家属给了我们充分的信任,我们谨慎分次的边化疗边严密观察,这个患者真的闯过了最初的死亡风险,回归了社会回归了家属。
虽然我没能彻底治愈他的疾病,但闯过了死亡关口,给了他家人莫大的安慰,也让他自己能好好地安排生活、家庭和孩子,与家人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否则从发病到死亡就几天的时间,这对家人太痛苦了。
03医学有限,努力无限
肿瘤医生对生命近乎“贪婪”,以至于无论自己帮患者延续了多长时间的生命,当患者真的面临生命终点的时候,医生都会感到无力、遗憾,甚至会把自己之前获得的所有成功都抹杀掉,总在想,也许这样治或那样治也许他还能更好、能更多的活一段时间。
这正这个职业的残酷。
每一个人对生命的追求都是无止境的,医生更加看重结果,于是会把每一例死亡都当作教训,经常去思考、分析、总结,甚至会让你终生难忘,觉得遗憾,而恰恰医学就在这些总结中发展,医生在总结中成长。
沈琳:
十年前,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得了和乔布斯一样的病——胰腺神经内分泌瘤。但他家里很穷,病情也比乔布斯晚,发现时已经满肝都是转移灶。
找到我时,消瘦的皮包骨,治疗一段时间肿瘤控制了,恢复的白白胖胖;过一段时间肿瘤又长了,人又消瘦脱相,又来治疗,控制后又回家。就这样,前前后后活了6年,乔布斯换了肝,生存期就是6年多,但他没有那么多资源,也没有那样的经济条件。
他的父母、姐姐,一家人都盼望他能健康地活着,我们也全力以赴为他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募集特效药。
这几年里,看到他身体恢复,全科医生都发自内心的高兴。
医学的局限我们最终没能够留住他,他姐姐给我发短信表示感谢,但我特别难受,几年的付出以及获得的所有成功和成就感都没有了,真的没了……
04在门外和走进来
治愈肿瘤患者的成就感,外科医生会强得多,但对肿瘤内科医生来说,正因为相对少,所以更弥足珍贵,也更幸福。
有些患者一年来复查一次,其实从医疗上他不用去看沈琳,可他们总是要跑去沈琳诊室报个到。患者看到自己的主治医生高兴,医生看到自己的患者健康地活着,更幸福,而且会幸福很久。
沈琳:
有一次,无意中遇到另一家医院的一位搞心血管病的老教授,听说我是搞肿瘤的,特别兴奋地说:“哎呀,你们肿瘤现在是不是有特效药啊?”
我说:“没有啊。”他说:“怎么没有啊,吃几片药就好了,跟我们高血压控制是一样的。”
我说:“是吗?”他说:“我身边那***就是。”
我说:“哦,他是我的患者。”他又说:“原来肿瘤也是能治好的,转移了也能治好。”
我说:“能啊,虽然还不是太多,但有些是可以治愈的。”
这个患者是遗传性胃癌,他妈妈和妹妹都在我们医院去世。他刚开始在别的地方治疗,后来听说还是北大肿瘤医院治胃癌好,就又回来了,当时已经出现手术后转移,他非常悲观。在我们这里综合治疗一段时间后,控制了,肿瘤几乎查不到啦,就用一种药物口服维持,两年多后停止了用药,现在近十年了,一直活跃在他的工作岗位。他岳母也是医生,和那位老教授是同一个科室的同事。
这个故事,沈琳记得特别清楚,学起这段对话,维妙维肖。她说,对肿瘤的认识,不仅普通人,就算是非肿瘤专业的医生,也有很多的不了解和误解。
肿瘤,从门外看都是没救的,其实当你走进来,你会发现可做的事很多。通过医生的努力,有些早中期的患者可以治好,有些晚期已经转移的患者,通过合理的综合治疗,也有部分最终能治好,回归自己常态的生活,走向社会,走向家庭;而对那些没有治愈可能的患者,医生也要以帮助他,让他们活的长,活的好、少有痛苦。
(统战部摘自医生医事 文/戴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