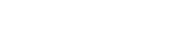“姜叔叔好!”
那个男孩也许不知道,当年,他骑着单车在医院门口偶遇“姜叔叔”的这一句问候,为所有中国的孩子留住了一位儿科医生,多年后,这位医生成为了国内神经系统疾病一位顶尖的专家——姜玉武大夫。
姜玉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这位著名小儿神经内科专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一批脑发育相关神经遗传病的分子遗传学诊断方法,在国内首次确诊并报道了既往国内尚不认识的3种神经遗传病。他担任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遗传委员会委员、国际儿科神经病学会特邀理事(整个大中华地区唯一代表)……
我记下了他办公室书柜的书目,一大半都是非医学的哲学、人文类;我记下了这位“姜叔叔”长在每个孩子身上的眼神,逗孩子玩时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
我记下了他常常1个小时马拉松式的问诊、解释和叮嘱;我记下了他在给出“目前无法治疗”结论时,面对流泪的患儿妈妈说“对不起”的柔软;
我记下了他推动小儿神经专业的努力;我记下了他说“外人其实难以真正理解医生”的距离感;我记下了一位患儿父亲拎着25万现金,要通过他捐给其他孩子的信任;
我也记下了他说“看病其实看的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感悟;我更记下了他说的:真正的乐观,是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着希望……
姜玉武教授的学术成就,可以在网上轻松搜到,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不花太多的笔墨来罗列。我希望用有限的文字来传递跟访他的日子里的感动,他对孩子、对家长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真诚理解与理想。
最了解孩子的一位儿科医生
看姜玉武和孩子交流,是一种享受。
一个1岁4个月不会说话的小宝宝刚刚睡醒,姜大夫转过身,靠近孩子,捏捏小耳朵:“宝宝,宝宝睡醒了啊。”宝宝开始兴奋起来,小腿乱蹬。他握住小手撑开小拳头:“这么棒,看看小手洗干净没。”然后,又挠痒痒肉,在宝宝咯咯笑时,顺势按按腹部“叔叔看看小肚脐还在不在啊”。再握住乱蹬的小腿,脱了袜子看看小脚丫……
姜叔叔一边逗孩子,一边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全部的查体。然后对旁边的学生说:脸形长、招风耳、平足,要注意脆性X综合征。
姜叔叔还喜欢考小朋友“分苹果”:你有3个苹果,分给爸爸一个,分给妈妈一个,你还有几个?
听诊器上的小猴子,也是姜叔叔的好帮手:“小美女,看看这是什么动物啊?”“猴几”“是猴几吗,不是狗狗吗?”“是猴几”,这个3岁多的小姑娘测试过关。
一对夫妻带6岁的儿子来看热性惊瘚,姜玉武一边提问、记录、判断、解释,一边随时关注着身边这个6岁多的淘气男孩。最后他说:这个孩子,我高度怀疑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病比你现在带他来看的单纯的良性热性惊瘚更需要治疗。家长十分惊诧,他们一直以为儿子仅仅只是非常调皮好动而已……
姜玉武就是这样,他的眼睛就像长在孩子身上一样,一见到孩子,雷达就全面启动,哪怕是在问家长病史,还是在记录,都能注意到孩子的一举一动。他如此观察了孩子23年,对孩子发育过程中的异常非常敏感,看孩子的眼神,也极让人感动。
40多岁的姜玉武教授,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的那场重病,他指着衬衫衣领下的气管处说:“我这里被切开过,上了呼吸机,差点死掉。”他患的是一种叫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周围神经病,全身瘫痪连呼吸肌都瘫痪了,无法喘气。医生救了他,他活了下来,长大后当了一名儿科大夫,去抢救别的孩子。
但在他刚工作几年后,也曾因为儿科大夫在社会和业界地位的问题,犹豫过是否继续当儿科医生,因为考博是一个机会,可以转内科,或者也可以出国。那天晚上7点多,他下班后在医院门口打车回家,一个高高壮壮的大男孩骑车突然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姜叔叔好”。“姜叔叔”很诧异:你认识我?男孩说:对啊,两年前您抢救我的时候,还安慰我别害怕啊,现在我特别好。
姜玉武才想起来了,这是两年前是一个特重的急性肾炎合并急性肺水肿的孩子,这种患者有一种濒死感,刚上小学6年级的孩子很害怕,姜玉武除了抢救以外就抽时间一直陪着他,安慰他说:“别害怕,有叔叔在,不会有问题的。”后来真的抢救过来了。
还有什么比一个濒死的孩子,两年后高高壮壮地站在医生面前更大的成就感?那一句问候,促成了姜玉武继续留在了儿科。
“干儿科有时候和当老师有同样成就感,你要把事情做到极致,他就可能被救过来,将来可能就是正常的孩子;你要稍微有点没有注意到,将来他就可能残疾,影响他一辈子。”姜玉武经常路过医院附近的西什库小学,总有小孩跑过来喊“姜叔叔好”,他还有几个20多岁的“干儿子”,他们是他的骄傲,也是他前进的最大动力。
充满“人生智慧”的门诊
听姜玉武的门诊,也是一种享受。
每周四的特需门诊,姜玉武几乎都要从8:30一直要到晚上9-10点。除了小儿神经专业的复杂性,医生对初诊患者的问诊要花极长时间外,更重要的是,姜玉武毫不吝惜解释的时间,从发病原理到每一种症状、治疗、预后,都尽可能希望解释清楚,甚至包括对年轻父母疾病观、人生观的引导。
由于智力发育、运动发育落后,神经类疾病的孩子很容易被歧视,北大小儿神经科的大夫,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在治疗孩子,更大程度是在治疗父母,他们看病很多都是在帮助家长减轻缓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
“我性格相对比较敏感,可能是小时候磨难太多造成的吧,所以常常能比较准确地感觉到其他人的感情波动,这可能不一定是好事,相对比较累,呵呵。但对于当医生来讲,可能是个优势,因为病人家长的一言一行我都能比较好地体会到他在想什么。”姜玉武说。
一个被姜玉武诊断为抽动障碍的3岁小女孩,这是一种良性病,不会对患儿生长发育和智力造成影响,但可能不由自主的动作太多而“不好看”,引发家长和患儿的心理障碍,尤其是妈妈,常常很很纠结。姜玉武特别叮嘱“切记不要过度治疗”,劝导说:生活从来就是不完美的,人要容忍不完美,容忍缺点,包括父母与子女、夫妻、同事之间,都是这样,太追求完美的人,容易产生挫折感。对于这种相对很良性的病,疏导心理可能比用药更重要,即使用药,也是对于发作比较重、比较频繁影响孩子生活、学习的患儿,而且也只需要明显减轻症状即可,否则用药过度,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甚至会超过疾病本身对孩子的影响,那就得不偿失了。通过详尽的解释,妈妈释然了很多,孩子也重新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姜玉武反复强调:我们是看病人,不是看病,我的老师们也一直是这样教我的。其实,几句话问完我大概也会知道是什么病,然后很快开药走人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家长如果不理解就不会执行得很好,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他的心理压力也一定会传递给孩子,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也就很大。这样就达不到我们治疗的最终目的。
“你为病人着想,他们都能感受到的。”所以,经常给病人治着治着,姜玉武就成了他们全家的生活参谋了,什么事都想让姜大夫帮着拿个主意。“我看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这个,这个没有价值吗?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因为我的目的是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希望他们不光病好了,还特别希望他们能够达到其生理水平能够达到的最佳发展。”他说。
当医生久了,随着自身人生历练的增加,姜玉武越来越感觉到,看病其实看的是一种人生哲学,“治病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搞清楚,其实治病的终极目的是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孩子来讲还有最好的学术发展(academic achievement),有时候如果仅仅盯着某个症状,比如癫痫发作,而不考虑病人的其他情况,比如药物不良反应、共患的其他疾病、甚至药物经济学因素等等,那样的话即使发作控制了,孩子或者家庭的生活质量不一定就明显提高。”
当医生久了,姜玉武也更加理解什么是生活,他说:生活就是有各种喜怒哀乐,有时候欲望太多,或者要求太高,就不容易获得满足感,也就是幸福反而就少。比如,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不切实际的高,提前设定了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孩子没达到,就不能面对或者接受,就有可能焦虑、抑郁,甚至导致整个家庭气氛紧张,全家都不幸福。
当然,现在整个社会高速发展、竞争压力大,对普通人都会压力很大,何况这些患病的孩子和家庭。如果社会能对这种弱势群体的生活有更多的保障,他们也就不会这么焦虑,就能够平心静气来接受治疗,平心静气地面对这种相对不完美的生活。
作为医生,姜玉武只能劝患儿家长去坚强地面对、适应这种生活,鼓起勇气多向好的方向看,去发现、珍惜、享受孩子给自己、家庭带来的感动和亲情。科室和协会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来支持他们,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为保障他们的权益而奔走呼吁。“但这些力量仍然很弱,还远远不够,需要全社会都来支持关心他们。”姜玉武真诚地说。
他也曾被病人告过
“直到现在我也一直非常热爱我的职业,个人认为医闹还是少见的‘极品’,正如生活中既有极品的好人也有极品的坏人。”姜玉武也遇到过医闹。
那时姜玉武29岁还在读博士时,已经是代理儿童重症监护室(ICU)的主治医生了,有一次从婴儿病房转来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合并严重肺炎的孩子,特别重,到ICU就上呼吸机了。由于想救这个孩子的信念特别强烈,于是姜玉武几乎天天守着,甚至有时间就亲自去吸痰、换气管插管等,几乎一个多月没回家。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容易呛奶,后来在五一放假期间,这次孩子再次意外呛奶后,原本脆弱的稳定被打破,病情一下子就加重了。于是,家长放弃了治疗,还反过来就把科室告上法庭,姜玉武作为病房主治大夫,也被告了。
更奇葩的是,家属在法庭上强硬地指责医护和医院,但是下来就跟姜大夫解释道歉,还非要请吃饭:“真对不起,我也不是真想告你,只是觉得孩子很珍贵,没了不能接受,而且这么长时间住院的费用太高了”。
“当时确实觉得伤心,真的是一腔热血啊。为了救这个孩子,我和病房的医护真的都全力以赴了,没有任何一点差错,到头来落到这个结局,所有参与的医生护士都很难过,既为这个孩子,也为这个孩子家长对我们的态度。”姜玉武说。
这件事,让姜玉武一段时间有些心灰意冷,是否还要这么全身心投入在这个职业上,是否还要对病人这么好,值不值?但很快,很多其他病人给他的鼓励和感动,又让他再次全身心投入了进来。
“我相信那个家长心里是不恨我们的。他也知道我们对病人尽力了,只是社会很复杂,他无赖也可能是没办法,只好跟医生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坏人,但一定是很少数,不是主流。绝大多数病人是真诚感谢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帮助的,而且也会回报感谢,这些正能量其实还是主流,也是我们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当医生,下辈子让我干我还是当医生。”姜玉武说。
其实很“愤青”
科里的医生悄悄说:其实,姜大夫很“愤青”。
一家长带着患癫痫女儿来看病,说:“我要有个儿子,我也一定不娶我女儿这样的女孩子。”
姜大夫“愤青”了:“你都看不起自己的孩子,别人怎么能看得起她?!”他常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遇到的很多家长,他说:“一方面他们的孩子被人歧视,另一方面他们还认同这种歧视,这非常可怕。”
一家长想去找某“中医”治病,说:我们亲戚的一个孩子,那个“中医”真的给看好了,用神经肽修复术,一个月就起效了。
姜大夫又“愤青”了:这可不一定对,尤其是神经肽修复术根本就子虚乌有。如果按你这样说,治好了几个病人就是神医,那我就是神仙了,我看好了多少孩子,至少得有成百上千吧,但我肯定不是神医,因为我也有没有治疗好的病人。所以,如果只根据治好的病人判断一个医生的好坏,就有可能出现明显的偏差,比如只告诉你一个医生治好了一千个病人,但是同时他还治死了一万个没告诉过你,虽然治好的很多,但是治死的更多,你说他是好医生还是坏医生。所以要么他告诉你一共治了多少个,治好多少治坏了多少,整体评价那才有意义;否则单说治好了多少个,别说几个、几十个、上千个我也不信。这不科学,有些骗人的假医生就拿这个来蒙人。
医生应该是最人文的职业,只有真正理解患者疾苦,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天悯人情怀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医学大家。姜玉武的办公室两套大书柜有三排书,最高的一排是医学专业类,最方便拿取的第二排,全是人文类的书,《人生有何意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给理想一点时间》《大民小国》……趁他接待访客的空当,我抄下他的书目,姜玉武笑着说:平时也没什么时间看,每次都是在旅途中飞机上带一本抽空看看,过过瘾。他在朋友圈曾引用一篇文章:我同意“我热爱读书的意义在于,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自己。只有读越多的书,看越多人的文字,只有体味更多的命运,洞悉更多的时代环境,才能让自己不依附于外力,不依附于当下,做一个思想独立的人。”
关于加号……
早上8:30,姜玉武刚进诊室,一个男人冲进来请求加号,姜玉武拒绝了,男人突然往下跪倒:“求求您,我都来了两周了,还是挂不上号。”姜玉武马上站起身扶起他:“我真的不能加号,今天的病人实在是太多,真看不完,如果你非要这样,那只能我先离开了。”
尽管这样类似的行为过激的请求并不少见,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这位谦和、书生气的学者教授面对这种行为依然的窘迫。
“你知道我为什么显得这么铁石心肠吗?”事后,姜玉武告诉我,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一次受他同学的启发,帮他下了这样的决心。同学说“给这样的病人加号就意味着对那些按程序挂号的其他病人不公平”,因为其他病人都是排很长时间的队或者持续打预约电话才挂上号的。
曾经,在还没有那么多加号病人的时候,为了和号贩子斗争,姜玉武起了蛮劲,谁来都给加号,“哪怕门诊出到晚上不睡觉我也要加”,但后来发现这样根本不行,病人太多了,他根本加不完。最重要的是,很多别的专家,甚至年轻大夫完全能看的病,也都非要找他看,其实是不必要的。如果真是其他医院按程序转来的疑难病人,确实需要他加号的,还是可以的。
跟访中的一次是姜玉武的全天特需门诊,36个号,从早上8:30一直看到晚上9:30。中午回办公室休息了1个小时,晚餐就是和学生在诊室随便吃点面包牛奶,10分钟解决问题,然后继续战斗。
他说:“不加号都看到这么晚,再加号,真的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了。我经常和病人说,我现在能省点时间多睡会儿觉,就可能多活几年就可以多看更多的病人,如果我再这么耗竭性的拼命的话,最终看的病人可能更少。”
尽管是下了决心,但每次拒绝,他心里都很纠结,甚至觉得有些愧疚,“过几年我不当主任了,我就能多看几个病人了。”他说。
对于一位医生来说,多加几个号就是多帮助了几位病人,但对于同时又是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和在学会任职的医生来说,帮助病人的方式,则并不仅仅只是“加号”。
姜玉武说:“我一个人就是不睡觉地看病又能多看几个?但如果我把我的知识教给10个人,就放大10倍,教给100个人就放大100倍;而如果我写了教材,就会影响一代学生;如果把科管好了,能有多少病人受益?如果我的研究发现一种新的疾病诊断方法、新的治疗方法,会有多少病人获益?”
当好科主任、带出好学生,帮助更多年轻大夫提高医疗水平,成为姜玉武最重要工作,作为大夫,他也希望尽可能多看几个病人。如何兼顾?
有一天,周二开了一整天的会,他下午6点赶回诊室,一直看到了晚上11点……
关于钱……
门诊里,一个从外地来的父亲带孩子看完病,开药,600多元,憨实的父亲说:“我先不拿药吧,没带那么多钱。”姜玉武说:“我先给你垫吧,以后你抽空再还我。”说得轻描淡写,就像把钱借给自己家人、朋友一样随意,让听的人毫无负担。
这个科的大夫经常私下借钱给病人的事,我们在采访中有所耳闻,这一次亲眼见到。
姜玉武说,科里的大夫大多数都有这样的经历。“这还是几百块钱的小数,那天病房一个小病人,脑膜炎,没钱了,病房主任回家拿了2万块钱借给他们救急。”他笑着说。
这个科的医生靠谱,病人似乎也靠谱,医生们借出去的钱从没打水漂过。姜玉武说:“我们科的患者家长和医生还是相互理解的,他们一时半会周转不开的话,我们也很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比如有些病人治不起,但又明明是能治的病,大家都会着急,那我们就先给凑点,先用着,什么时候能还再还。”
还是关于钱……
有一天,一个男人拎了一个大兜来到姜玉武大夫门诊室,把门一关,说:我不是来看病的,我的孩子已经好了。这是25万,您看哪个孩子缺钱,您就给他们用。
姜玉武回忆起这件事,笑着说:“吓得我一哆嗦,马上说,这哪行,你这不是害我嘛。他说,你建个账户,我给你打,我说也不行,万一别人说这是病人给我行贿,我就说不清楚了。”
这位患儿家长执意要捐钱,姜玉武说帮他联系一个基金会吧,但他说:“不行,我信不过他们,我只信你,只要想把钱给,你随便花,我相信你会给病人用的。”最终这个钱还是让家长拿回去了。
还有一名癫痫患者的家长,在国内找姜玉武看病,也常去国外看病,并给美国癫痫病协会捐了1亿元。姜玉武很吃惊:这钱为啥不捐给中国?对方说:“你从没和我说过啊,只要您号召,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来捐钱。”
姜玉武这时忽然意识到:对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国外一样,呼吁有经济能力的人来帮助那些需要救治的孩子呢?
于是,这位“姜叔叔”又增加了一个帮助孩子的新想法:希望能跟医院申请、通过医院和某个基金会合作,建立一个“儿童神经科疾病基金”专项账户,双方共同管理,公开透明,医院科室共同参与资金使用管理。
他说:“神经科的病人有些真的很可怜,尤其是能治而没有钱治的时候,虽然不一定能100%治好,但如果能坚持治,大多数还是有可能显著好转的,但也可能花了很多钱最后失败了。这种情况,很多家庭就会犹豫。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帮他一把,哪怕是一个阶段,他看到的确见好了,这就会有信心往下走。”
治疗一个孩子,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承担的是一个家庭的信任和希望,而成立一个基金,则意味着要承担更多人的信任和希望。
对于目前大量的无能为力的神经系遗传病、罕见病的孩子们来说,姜玉武和他的医生伙伴们,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这就是一份希望,这才是真正的乐观。他们正在一起努力,争取为这些神经系统疾病的孩子尽量撑起更大的一片蓝天,让他们也能享受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充满希望的童年。
(统战部摘自医生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