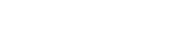在北大医院抗击“非典”一线,活跃着一位被前线勇士称为“保护神”的白衣战士,她就是健康教育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李六亿。自从北大医院成立SARS病房以来,她一直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
这里危险,我先检查防护,你们再进去
最初北大医院接受成立SARS病房(即感染三病房)的任务时,很多防护物资还没有到位,但大批的患者已经转了进来。医生和护士刚要进去检查病人,李六亿发现防护服还没有准备好,就拦住他们,说:“不行,这里危险,我先进去,检查防护情况!”说完,她加了一个一次性口罩和帽子,戴上手套、鞋套,穿了件一次性手术衣就进入了病房。她一间接一间地认真检查,嘱咐每一个病人都戴上口罩,告诉他们不要随便离开房间,大小便的时候都注意些什么。转一圈出来后,她还是有些不放心,嘱咐所有进去的医生护士一定注意防护自己,如何穿、脱手套、鞋套,如何摘和戴帽子、口罩,怎样在没有严格的防护隔离服到位之前使用一次性手术衣进行防护,如何减少交叉感染等等,并且自监督他(她)们穿戴整齐进了病房。
作为全国感染管理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李六亿,早已成为这个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作为中华感染管理学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北京市抗“非典”专家组成员,她对SARS的传染性了解最多,更深知科学防护对于一线战士的重要性。在防护未完全到位,而病人已经进驻时,她更明白医护人员所面临的危险,她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先冲了进去,把能够采取的防护措施提前做好,尽最大努力减少一线战士的感染可能。
最惦念5岁的儿子
从那时起,李六亿就再也没回过家。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5岁的儿子牛牛,幼儿园早就放假了,孩子只能天天呆在家里,她总觉得对不起儿子。牛牛天真可爱的笑脸时常浮现在她的眼前,她有时甚至不敢接他的电话,生怕儿子听到自己的哭声。一次,牛牛在电视里见到了妈妈,兴奋地要和妈妈说话。可电视上的妈妈没有反应,牛牛伤心地说:“妈妈,你为什么不理我!”李六亿说起这事时,眼圈都红了。
李六亿的爱人从来都是大忙人,连周末也常常在外加班。远在老家的妈妈身体不大好,只好派来了表妹的女儿来帮助照看牛牛,解了她的后顾之忧。
李六亿说,我虽然不是医生、护士,不能亲自治疗病人,但疫病当前,我们也必须冲锋在最前线,以保护一线战士们的身体健康,和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一样,我们也都做好被感染甚至牺牲的准备,但最让她牵肠挂肚的还是儿子。
我们是讲科学的
被委派到胸科医院后,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里是病床总数仅次于小汤山的全国最第二大SARS定点医院,收治来自全市各医院转来的500多位患者。在北京市卫生局的亲自领导下,成立了胸科医院隔离防护专家组,李六亿任专家组组长,负责管理由多家医院共同管理的胸科医院内的隔离防护措施。
首先是要摸清情况。为此,她不顾危险走遍了所有的病房,随时解决隔离防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防护不合理之处提出严重警告和具体改正措施。
她发现,每家医院的防护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些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保护自己而不惜多穿到5-6层隔离服,这样反而放松了警惕而容易被感染;同时天气逐渐转热,容易出现虚脱甚至中暑;而有些医院的防护措施又远远不到位。再比如穿隔离服的流程,先穿哪件、再穿哪件,都是很有讲究的,穿得不对很容易被感染。
为此,她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制定了防护流程,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讲,有时一天就要讲3-4次,这些天嗓子总是沙哑的。很多医院热情地请她去讲课,但她又实在抽不出时间;令她感动的是,在北医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她讲解的录像已经刻制出光盘,大家可以从光盘上直接学习自我防护的正规操作。
有一次,一直忙到大半夜、刚刚睡下的她被电话叫醒,让她火速赶往某病区。原来是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不遵守病区防护操作流程,把清洁区都污染了,还为此跟医务人员吵了起来。李六亿赶到后,严厉批评了他们,指出不按照操作流程进行防护就是犯罪,会造成大批医护人员倒下。
一个流调人员还在嚷嚷,“我们是中央派来的,我们懂得如何防护!”
李六亿急了,“中央派来的怎么了,我们是讲科学的,在这儿就得听我的!”
此时,十几年来从没因工作问题掉眼泪的李六亿大哭了一场。随后,她又和医护人员一起对被污染的清洁区和半清洁区进行了严格消毒。
由于她的严格把关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两周多来战斗在胸科医院抗“非典”一线的北大医院医护人员还没有一位出现感染。
她一再强调,“我们是讲科学的,任何不慎都可能使大批医护人员倒下,付出血的代价!我一直觉得自己难以承受肩头之重。”
自从冲上前线以来,李六亿再也没有睡上一个整觉。她说,看来我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了,现在最大的心愿是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珍贵的防范意识
在他们用生命拉起的安全屏障之下,春光依旧抚摸着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2003年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当时北京的医生对于这种肆虐广东并初露狰狞的烈性传染病,已经警觉。按照《传染病法》的规定,传染病当由所在地的专业权威机构做出“判决”。
当时,医院拿到的“权威”报告是否定的结论。也因此,病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取消隔离、消毒、转院等全套措施。
但是,这里毕竟是北大医院,是有着88年历史、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临床医院。行内人很清楚,因为“近水楼台”,医院年年吃“头茬韭菜”。日积月累,这里有着非常雄厚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积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第十七届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在疾病的恶性流行期。当然,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先隔离,后诊断。非此,又怎能切断传染源?
医院还是对病人采取了隔离措施,你不隔离,我自行隔离。3天后,病人症状凸显。“权威”机构只得回过头来把结论推翻。有些玩笑是开得起的,但是在“SARS”面前,那将是成片的大活人束手就擒。直到今天,院长章友康想到此还心生恐惧:如果当时稍有大意,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有的医院”真的很惨烈。就因为一例“病毒王”,致使扩散的速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挨着他的人依次倒下。而其中伤及最严重的是医护人员。一场战争还没有打响,一个重型装备师却先失去了作战能力。
其实,还在羊年闹花灯的时候,北大医院这所学风朴实的医院,就已经开始“SARS”战前总动员。有关培训一天4拨。300人的课堂,拨拨座无虚席。他们的口号:“SARS面前人人平等”。这在日后应对抢救的时候,被证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包括医院的行政,后勤,保安,护工,无一例外都在培训之内。
在我国,传染病的防治概念,不要说老百姓,就是一些专业人员也已淡漠。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疾病在人们的意识里,似乎已荡然无存。自从中国宣布基本消灭麻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综合医院几乎都已关闭了传染病科。全市仅有的两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都没有相应的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的必备条件和设施。
这是“SARS”最可恨的一点——它抓住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于是,当病魔向我们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们窘迫,慌乱,措手不及。但是,从良心上讲,它给了北京人相应的准备期。如果在广东流行的时候,我们的某些管理部门,能够有更强的责任感和更敏锐的目光,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事后很多专家都看到这一点——对于突发疫情的暴发流行,我们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制和条件。而北大医院是北京惟一保留了传染科的综合医院。特别是在会战疫情的非常时期,他们“哗”地甩出“三驾马车”。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实力让人觉得,难道这帮人早已料定会有“SARS”入侵。
从容得多。差距从根本上拉开。除了前面说到的“传染科”,医院另外的两支队伍是“感染管理科”和“呼吸科”。这“三驾马车”,从“防”到“治”,即从切断传染途径——降低感染率;到治疗效果——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养兵千日,即在用兵一时
用知识筑起防护的长城(医护人员感染率2.2%)感染管理科是北大医院的强项。在和平时期,在以抢占尖端的科技为荣的竞争时代,这所医院始终没有对基础管理稍稍放松。“感染”是自打有医院以来最古老的话题,但是感染管理又是医院永恒的主题。它是体现一个医院实施医疗服务的内在真功。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亿,1995年引进的人才。这是一位非常可爱且年轻的女学者。从4月10日,医院抢建临时“SARS”病房开始,她就再没有回过家。有时爱人抓着电话筒不放,“不能见面,还不能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么?”没有办法,现在她的每一分钟不属于自己。她的吐字,从嗓子里出来,带着劳损而撕裂的血丝,可以让每一个听话的人心里战栗。
你能看得出来么,这么一位儒雅女子,在这场与“非典”的战役中,竟是先头部队的总指挥。隔离——第一道最要命的防线是由她这样的专家拉出来的。真的,她就像临战的将军,一时间院内大牌的教授、专家都望着她,“六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3天时间,她参与完成了医院的“SARS”病房临时改造任务。之后,她又冲到北京市胸科医院,担负起第二轮的改建工程。之后,中日友好医院在胸科开设的SARS病房的改建工地,依然有她的身影。北京人应该庆幸,在一个由多家医院联合作战的大场面,这位感染学专家有机会从一家医院走出来,推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她的种种设计方案和防护理念很快被大家认可。此前,各路有各路的高招,有些医院防护服可以套到五层六层之多。赶上高温天气,一天热晕过去的医护人员就有好几名。
“三层防护服是有道理的”,李六亿这样解释,它是与三个不同的空间流程相配套:贴身服对应清洁区;防水服对应半清洁区;隔离服对应污染区。多一层则“赘”,少一层则“险”。号称“多国部队”的胸科医院其他几家,觉得此说精当而有理,于是纷纷效仿。
李六亿的“三层防护服”还真的遭到过冲撞。一天半夜3点多,来了一路人马。同样是为了“SARS”,急需接触北大医院的病人。病区值班员与来人发生争执。一则,病人都在休息;二则一哄而上30多个,容易交叉感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防护措施不符合医院相关规定。来人流露出对“三层防护服”的蔑视。他们宣称,我们从来是“一层衣服”走遍各个医院病区,畅通无阻,“就数你们这儿事多”。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李六亿被惊醒。她明白这些人需要培训一下。她不急不慢地说,可以,我让你们进去。但是,需要提醒一句,到时候你们打算从哪儿出来?如果从医护人员通道出来,对不起,按我们的规定,进入半清洁区,要脱一层;进入清洁区,又要脱一层。真的,李六亿心里暗笑,这些人只穿了一层衣服,他们怎么脱?没得脱呀。来人细细琢磨了一下,自行告退。
除此而外,在安装排风扇的位置上,她也有特别创意——把排风扇安在房间的下部。理由是起尘的层面要放得比较低,这样有助于呼吸层空气质量。同时,她别出心裁,将低臭氧紫外线灯,调个个儿,反向安装。这算得上是急中生智。打破常规的做法,扩大了消毒灯的有效使用价值,因为是反着装,即使人在,也照样可以照射。空气消毒便可以不间断地持续。
她设立的监督员制度,也备受推崇。监督员会提醒医护人员,在哪个区,该怎么做;死亡病人该怎么处理;被**怎么应对……如此可以避免因为防护程序繁杂,而乱了规程。对于一线人员大大增加了安全感。
据说,因为是情急之中,又盛情难却,这些日子李六亿马不停蹄。她从这家医院到那家医院;从改建工地到中央电视台,指导、讲学、办班。当然也因此,她被“多国部队”推选为北京胸科医院的感染管理专家组组长。
医院参战“非典”的一线工作人员771名,感染人数24名。其中7名是无关感染。按17名计算,医院感染率仅为2.2%。而这17名中有15名是在极特殊的无隔离条件下感染的,因此真正的病房感染人数只有2名。从互联网提供的资料显示,“非典”初期,某地区医护人员感染率高达33%;就是在后期加强防护之后,医护人员感染率仍在24%。
李六亿是中华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参与过国家医院感染管理的标准制定工作,并亲手起草过一系列规章、条例。美国1996年修订的“标准预防”法案,其翻译及引进工作也是由她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