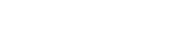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我作为实习医生第一次走进病房和病人直接接触。这是一个简易的单人病房。并不宽敞的病房里,一张病床占据了整个病室的大部分。床上躺着一个女病人。她消瘦,两眼微闭着,脸色阴沉晦暗。带教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50多岁的工程师”,肺癌正吞噬着她原本健壮的身躯。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单独采集病史,我在狭小的房间内感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半开半闭的窗帘加上天气寒冷,窗户紧闭使室内狭小的空间弥漫着一种阴冷的感觉,夕阳从不大的窗缝中不大情愿地探进头来。血色残阳映照着一个无助的男人,这是病人的丈夫。他一直垂着头,长吁短叹。
“您好,我是新来的住院医师,我能和您谈谈吗?”我对病人说,但是她并没有理我。眼睛稍微斜了我一眼。“大夫,她刚服过药,有点不舒服。”她丈夫对我说。
屋里一片沉寂,只有电视机播送着中国女排的实况转播。“今天排球结果如何?”,我实在是怕这样的尴尬,找个话题和她爱人说。没想到的是,病人听到我的话,突然睁开了说眼,“您很懂排球?”我问,她立刻来了精神,“我大学时是校排球对的主攻手呢!”,病人一扫刚才脸上的阴霾,和我谈起了她大学时代的排球生活……。我当时想,这个晚期癌症病人也够可怜的,干脆找个她高兴的话题聊聊吧。她真的很高兴,说到她的大学生活,她神采飞扬,甚至坐起来和我手舞足蹈起来。我附和着她的话题,时间过得挺快,护士推门叫我“刘大夫叫你去一下”,我忽然意识到该干的正事还没做呢,走出病室,我寻思着如何向老师交待,病人的丈夫随后跟着我出来,他突然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小顾大夫,真的太感谢你了”,说着他眼里的眼泪落到了我的手上。我糊涂了,我说,“没没什么,我只是个实习大夫,我没有做什么呀?”“不,小顾大夫,是你给她带来了快乐,今天下午这几十分钟,是她半年来最高兴的一天!你知道,她是肺癌晚期,您虽然没有给她什么治疗,但是您带给她了真正的快乐,在她最后的日子,我们每天度日如年,今天她真的是很开心!您知道,这几十分钟对她多重要?我们家属没有别的奢望,只要她高兴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安慰!”短短的几句话,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肿瘤外科医生,我治疗过无数的病人,但这个病人的印象给我最深。我在思考,为什么几句与疾病无关的话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二十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学从注重疾病本身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心转变的核心是现代医学不仅要关注病人身体里的疾病,更要关注因疾病带给病人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对于一个肿瘤病人,他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因肿瘤带给他的死亡的恐惧、甚至有人说,肿瘤病人一半是因疾病发展病死的,还有一半是被肿瘤吓死的。面对一个肿瘤病人,我们做医生应该关系的不仅仅是病人的诊断,治疗方法,药物选择,我们应该学会关心病人的心理感受,他能接受肿瘤这个事实吗?他能够正确面对即将面对的各种治疗吗?如何让我们的病人坦然面对疾病,肿瘤和死亡?
一个人得了病,所有的人包括家属和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患的疾病身上,病人的父母会想到如何满足生病的孩子最后的愿望?做子女的会想到如何让亲人尽快接受手术?病人的单位领导想到如何处理善后的一切事宜?于是,癌症患者的家庭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齐心协力,对肿瘤隐瞒到底。但又有多少人去能真正体谅病人自身的真实感受?他们的彷徨,恐惧,他们的失望和焦虑?此时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物质需要,他们最需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人们忽略的恰恰是这个方面的考虑。对肿瘤的隐瞒使家属和病人承受双重痛苦,但这种做法是最常见的。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告诉我们的医生们,我们除了高超的技术,过硬的手术技巧,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训练,掌握相关心理学,伦理学,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人文”的意思是理想的人性,理想的人。一位有经验的肿瘤科医生曾告诉我如何安慰即将离开人世的病人:“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列正在运行的列车,把那些生病的病人比作即将下车的乘客,那我们会对生病的病人说,我们是在一个列车上的朋友,人生就是这样,有上车,也有下车,人总得下车,只是早晚。我们今天在一个车上,明天我们都可能在车下某个地方见面。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享受每一天。您想想,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高兴呢?”我们要用这样的话去鼓舞我们的病人,这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统战部摘自北医新闻网)
注:顾晋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